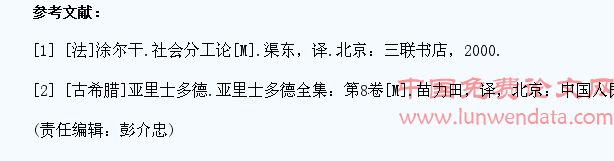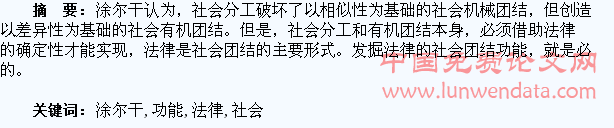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06??0126??05
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09SFB2007);湖南社科联项目(0804029B)
作者介绍:李伟迪(1964-),男,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怀化学院政法系教授。
1、涂尔干的社会分工
涂尔干说:“所谓分工,就是去分担以前的一同职能。”[1]但这里的分工,指社会分工、高级分工,它形成了两个趋势:其一,从业职员只从事一项社会商品生产销售工作多环节的一项,高度专业化;其二,因为专门从事某个环节工作,从业职员本项工艺的水平遥遥领先,就像别人在其他某项工艺上遥遥领先一样,出现了高度技术化。
为何会出现社会分工?“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缘由,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可以不断进步,是由于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常见扩大。”[1]社会容量指社会生活空间,社会密度指社会人口密度。从静态意义理解,生活空间与人口密度成反比,但在涂尔干的动态的历史语境中,是同步进步的趋势,确实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空间愈加大,人口密度也愈加大。为何社会容量扩大能促进社会分工?由于原来的蛮荒之地目前也能居住人了,如中国古时候早期长江以南被视为烟瘴之地,不合适人类居住,但南宋将来,长江以南变得比长江以北愈加兴盛了。既然新的地域可以存活,原始社会以来的氏族成员不敢离开氏族生活地区半步的限制被渐渐打破了,一个生活群体的成员可以在群体外存活,甚至更好,有点类似今天外出务工农民的转化。找到新的生活空间的成员,可能从事或创造新的职业,如此分工就出现了。人口密度为何能促进社会分工?“社会的成员越多,这类成员的关系就会愈加密切,他们的角逐就会越残酷,各种专门范围也会飞速而完备地产生出来。”[1]人口密度越大,既有平均生活资源就越小,角逐就就越残酷。“两个有机体越是相似,就越容易产生激烈的角逐。正由于它们有着同样的需要,追求着同样的目的,所以它们时时刻刻都陷入一种相互敌视的状况中。”[1]残酷环境日常的人,会绞尽脑汁求得更好的存活和进步机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机会在服务之中,因此,他或她会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找到一个更合适我们的工作或职业,或创造一个更合适社会的商品,于是,分工出现了。因此,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是什么原因的剖析是基本正确的。但,假如深究一步,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扩大是什么原因什么?是否社会分工?一定是。那样涂尔干是不是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困境?不是。我觉得,社会容量、社会密度、社会分工三者是互为条件的。
2、社会分工与社会团结的关系
涂尔干说:“社会的凝聚性是完全依赖,或至少主要依赖社会分工来保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点也是由分工决定的。”[1]“非但每一个人,每一个阶级,而且从多种角度来讲,每个民族都同时加入到了分工行列中,每一个人都以我们的方法,以特殊而又确定的程度,加入到雄心勃勃的公共事业中。它注定要渐渐地进步起来,以至于把今天的合作者与过去的先行者,与将来各种各样的后继者结合在一块。如此,人类的不同工作就会不断得到分配,它构成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原因,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一天比一天扩大,一天比一天复杂的最重要缘由。”[1]涂尔干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社会分工成为了常见现象,全体社会成员都参加到了社会分工中间;第二,社会成员参加社会分工,以我们的特殊性,确定我们的工种或职业;第三,社会分工是创造团结社会有机体的主要原因。
涂尔干承认在社会分工之前,也存在社会团结,甚至非常团结,比如家族。由于“只有我的意象和别人的意象相互符合,大家两人之间才会形成一种团结。假如这种符合源自两个意象的相似性,就称作粘合。这只不过由于两个意象在整体或部分上相互类似,可以紧密地连结在一块,完全融为了一体。总之,它们也只有通过这种融合形式才能相互结合。”[1]涂尔干的这个看法是一个社会事实,家族社会的团结感比目前任何一个团体的团结感强得多。家族社会的衰落,过去被理解为国家的衰落,如近代中国。家族社会衰落之时,恰好是社会分工兴趣之日,因此,学者们甚至把社会分工视为社会分裂、国家衰落是什么原因。但涂尔干与这个看法恰好相反:“不过,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状况却恰好相反,它们之所以可以结合在一块,是由于它们相互独立,相互有别。它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而源自这种感受的社会关系也不尽相同。”[1]
为何社会分工可以促进社会团结?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弄了解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种类。他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二类。在涂尔干看来,机械团结是一种较弱的社会团结形式,在早期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社会相似性程度非常强,见到了一个土著印第安人,就见到了所有些印第安人,也有点像马克思说的麻袋里的土豆。相似性为何产生社会团结?“是由于所有个人意识具备着某种一致性,构成了某种一同种类,这种型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一种社会心理种类。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群体成员不只由于个人的相似而相互吸引,而且由于他们具备了集体种类的生活条件,换句话说,他们已经相互结合成了社会。……如此,就产生了一种固有些团结,它源自相似性,同时又把个人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1]
涂尔干倡导的另一种相对进步的团结种类是有机团结。伴随集体意识的衰减和社会分工的进步,社会团结的唯一趋向只能是有机团结。这种团结中,“每一个人都拥有我们的行动范围,都可以自臻其境,都有我们的人格。如此,集体意识就为部分个人意识留出了地盘,使它没办法规定的特殊职能得到了确立。这种自由进步的空间越广,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一方面,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其次,个人的活动越加专门化,他就越会成为个人。……这种团结与大家所看到的高等动物是何等相似啊!事实上,当每一个器官都获得了我们的特质和自由度的时候,有机体也会具备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它的每个部分的个性也会得到印证。借用这些比,大家就把归因于劳动分工的团结称为‘有机’团结。”[1]
为何相似性产生团结,而差异性也能产生团结?“有的人觉得友爱是相同性,朋友一直相同的,他们说‘相同种类相聚’,‘意气相投’,与诸这样类的谚语。反过来,有人则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对于这类,有人想得更高中一年级筹,更深一层,欧里庇得斯说:‘干涸的大地渴望甘霖,充满雨水的天空渴望大地’。赫拉克利特说:对立之物总相一致,最好看的的和谐源于对立,万物由斗争而生成等等。”[2]这种说法非常实又非常虚。其实,这里有两个相反的趋势:家族之间的联系愈加少,呈离别趋势;社会联系愈加多,呈团结趋势。社会力量愈加强于家族力量,整个社会呈团结趋势。这就是梅因所说的,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社会联系为何愈加密切?“为何个人变得越自主,他就愈加依靠社会?为何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就越加紧密?”[1]根本缘由是社会成员生产的自用的商品愈加少,依赖别人生活的商品愈加多;同时,我们的生产过程与别人的生产愈加广泛地、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社会分工中,有机团结为何能取代机械团结?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古时候社会占据优势地位的机械团,过渡为工业社会占据优势地位的有机团结。整个进步过程呈现的是机械团结不断衰微、有机团结不断增强的过程。分工程度的提升使大家之间的差异愈加大,独立意识也愈加强,集体意识愈加困难,打造在集体意识基础上的机械团结日益式微。社会分工削弱大家之间传统联系的同时,又以一种新的方法,并且在一个比以往更高的程度上将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此时社会团结纽带就是由劳动分工的进步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在职能上的依靠。“劳动分工的最大用途,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法提升了生产率,而在于这类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用途,形成有机团结。”[2]
3、社会分工与法律的关系
涂尔干说:“即便分工产生了团结,也不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由于它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买卖代理人。更要紧的是,它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可以永久地把大家联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就像社会相似性产生了法律和道德,并以此来保证这种相似性一样,分工也产生了各种规范,可以保证相互分化的各种功能进行稳定和正常的协作。[2]他觉得,分工产生了社会团结的可能性,但达成这个可能性,需要法律规范。
以工业社会的契约为例,涂尔干觉得没社会力量的支持,没法律的强制规范,契约双方可能陷入混乱。分工的后面是契约,契约的后面是法律,法律的后面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涂尔干觉得,“当大家与社会发生连带关系时,社会是由一些特别而又不一样的职能通过相互间的确定关系结合而成的系统。”[2]
涂尔干通过批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斯宾塞的契约论,来证明契约的法律需要。涂尔干觉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只不过一种臆造。“毫无疑问,大家之所以通过契约结合在一块,是由于或者简单、或者复杂的劳动分工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需要。倘若他们想要相互和谐地进行合作,单靠彼此的关系与对彼此依靠关系的意识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在契约的整个有效期内对合作条件作出规定。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都需要得到确定,大家不只要考虑到缔结契约当时的现实状况,而且要估计到以后或许会产生或者发生变化的各种状况,不然在实行契约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会产生碰撞和口角。”[2]“大家假如只依赖已经确立的契约来发生关系,那样由此产生的团结只能是粗心大意的。但,有了契约法,大家尚未确定的行为也就有了法律上的结果,它表明了达到平衡状况所需的一般条件,这类条件是从平时的案例中渐渐形成的。”[2]
“契约所具备的维系力量,倒是社会交给它的。倘若社会并没认可契约所规定的义务,那样它就会变成只具备道德权威的纯粹许诺。”[2]“假如没法律的规定,假如没社会的存在,大家还能达成各种契约吗? ”[2]
涂尔干觉得社会分工前后的社会关系不同,法律种类也出现了非常大变化,从法律制裁角度,可分别称之为压制法、恢复法。“制裁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打造在痛苦之上的,或至少要给犯人带来肯定的损失。它的目的就是要损害犯人的财产、名誉、生命和自由,或者剥夺犯人所享用的某些事物,这种制裁称为压制性制裁,刑法即是一例。……第二种制裁并未必会给犯人带来痛苦,它的目的只在于拨乱反正,即把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重新恢复到正常状况。它借用强力挽回罪行,或者将它斩草除根,即剥夺这种行为的所有社会价值。因此,大家应该把法规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压制性制裁,另一类是纯粹的恢复性制裁。第一类包含刑法,第二类包含民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任何刑法都不应该划入到这类中来。”[2]
涂尔干汇总了社会分工与法律进步的规律,分工越发达,恢复法越多,压制型越少。也就是一般说的,社会越发达,民商法越多,刑法越少。“集体种类越能得到彰显,分工越是停留在低级水平,压制性法律相对于协作性法律来讲就越占优势。相反,假如个人种类越能得到进步,工作愈加专门化,那样两种法律种类的比率就势必会颠倒过来。”[2]
4、法律与社会团结的关系
涂尔干觉得,法律是社会团结的表现形式。“正由于法律表现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所以只须把不一样的法律种类区别开,就可以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团结种类。同样,大家可以确定,法律完全可以对劳动分工所致使的特殊团结作出表征。”[2]
涂尔干把社会团结的种类与法律的种类对接起来,压制法表现机械团结,恢复法表现有机团结。“我把规范划分为两类型型:一种是与压制性制裁有关的规范,包含分散种类和组织种类;另一种是与恢复性制裁有关的规范。大家已经看到,前者表现出来的是从相似性中产生的团结条件,大家已经将它称作是机械团结;后者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否定的团结,大家称之为有机团结。……法律和道德就是可以把大家自己和大家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它可以将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个具备凝聚力的团体。”[2]
涂尔干觉得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是体现社会团结的重点所在。“事实上,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生活都不可防止地会形成一种限制形式和组织形式。法律就是这类组织中最稳定、最明确的形式。普通社会生活的不断扩大,势必同时随着着法律活动相应地增加。因此,大家一定会发现所有社会团结反映在法律中的主要变化了。”[2]涂尔干这个看法,从现在的事实看是成立的;但从理论如何证明,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将来此看法是不是成立,有待研究。
涂尔干为了证明恢复法对工业社会的有机团结有哪些用途,先铺垫性地讨论了法律对家族社会的机械团结有哪些用途。他以刑法为例,“存在着两种遭到这种法律禁止和谴责的犯罪行为:在当事人与集体种类之间直接存在一种强烈的差异性;或者当事人触有代表一同意识的机关。这两种行为所触犯和违抗的力量是一致的。它是最根本的社会相似性的产物,它有哪些用途就是维护这种相似性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刑法就是要保护这种力量,它在任何状况下部不至于衰微下去。[2]
涂尔干形象地描写了保护一同意识的刑法推行及社会团结的具体过程。“正是犯罪,把那些真诚的意识团结在一块,集中在一块。大家只须看看,特别是小镇里所发生的伤风败俗的事情就足够了。大家一直停下脚步,走家串户,或者在特定的场所来津津乐道这件事情,如此,一种一同的愤恨情绪就表现出来了。……假如那些决定反抗用途的感情是很确定的,那样它们就会很一致。因此,这种一致性最后使大家相互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结合体,变成了每一个人的替身,但借助这个替身的并非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社会以此方法构成的群体。有很多历史事实可以证实这种惩罚的由来。[2]
在这里,涂尔干表达了四个意思:第一,犯罪使民众愈加团结,缘由是犯罪伤害了民众的一同意识,也就是说一同情感。犯罪的这种客观功能像鲶鱼效应。第二,犯罪导致的伤害越紧急,民众的团结感就越强烈,惩罚就越激烈。第三,惩罚最早也有分散的形式,后来渐渐过渡为集体形式,就是刑罚。第四,刑法就是代替个人的、分散的惩罚,以集体的名义出现的惩罚,目的是保障社会团结。
压制法为何转化为恢复法?“协作性法律和恢复性制裁所规定的关系,与它所体现的团结,都是从社会分工中产生出来的。由此大家可以概括指出,协作关系不再会实行其他形式的制裁。专职工作的特质就是,它摆脱了集体意识的影响。……假如这类职能愈加专门化,那样可以知道所有职能的人将会愈加少,因此,它们也会愈加游离于一同意识以外,确定这类职能的法律也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也不再可以惩罚犯罪,需要抵偿了。”[2]这也就是说,压制法只所以转化为恢复法,第一,根本缘由是社会分工,集体意识的基础没有了。第二,集体意识没有了,一同的愤怒也没有了,一同感受的伤害也没有了,维护机械团结的刑法也就没必要了。第三,机械团结式的压制法需要没有了,但新的即有机团结式的恢复法需要产生了。
“恢复性制裁的特殊性质已经足以说明与这种法律相应的社会团结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的。区别这种制裁的标志就是它并不具备抵偿性,而只不过将事物‘恢复原貌’。违反或拒认这种法律的人将不会遭遭到与其罪行相对应的痛苦;他仅仅被判处要服从法律。假如某种罪行确实已经发生,那样法官就应该将它们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他只能宣布法律,却不可以谈到惩罚。赔偿损失的处罚本身并没刑罚的性质:它只是拨回时钟返回过去,尽量地恢复正常状态的一种方法而已。”[2]这也就是说,涂尔干觉得恢复法与压制法有什么区别主要在于:第一,压制法是惩罚性质,恢复法没惩罚性质;第二,前者的机制是施加痛苦,后者的机制是恢复正常状态;第三,前者保护的是群体的一致性和机械团结,后者保护的是交换的稳定性和有机团结。第四,前者保护方法是主动出击,后者的保护方法是等待求助。涂尔干的恢复法主要指民商法,就此而言,也有部分法律具备惩罚性质,如《买家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双倍返还价款规定,合同法中的定金罚则,也有类似性质。当然,就主要而言,民商法的惩罚性微乎其微,涂尔干的看法是成立的,并且这个看法是以民商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数目居于优势地位而言的。假如比较现代民商法与刑事法的重要程度,哪个也不可以证明民商法比刑事法要紧,且民商法的背后就是刑事法。就此而言,涂尔干的看法是非常牵强的。
涂尔干觉得,有机团结可分为二类:物的团结,人的团结。前者是消极团结,后者是积极团结。前者主要通过广义的物权法体现和保障,后者主要通过契约法律体现和保障。后者比前者更有益于社会团结。维持相似性的机械团结也是积极团结。
“大家就能看到‘物’的团结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了:它把物与人直接关联起来,而不是把人与人关联起来。最极端的情形乃是:有人只相信世上只有自己一人来单独行使物权,而置别人于不考虑。因此,物只能通过人作为中介将自己整理于社会,而这种整理所产生的团结则完全是消极的团结。它没办法使个人的意志趋向于一个一同的目的,而只能按肯定次序把物排列在个人意识周围。既然大家以这种方法限制了物权,它们就不会相互发生冲突;争执被预先防止了,但大家之间却不再会有积极的协作和共意了。让大家尽量地设想一下这种相互妥协的景象吧;假如大家真的可以相安无事,那样社会就会像一团巨大无比的星系,每颗恒星都按我们的轨道运行,从没有妨碍其他恒星的运动。这种团结并没把各种要点联合起来,形成行动一致的实体,也没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它对社会机体的统一性从未作出任何贡献。”[2]
对积极团结的定义,涂尔干笔墨不多,但讲解的意义非常重要。“假如大家把刚刚讨论过的规范同恢复法划分开来,那样恢复法本身便还会包括一种确定的法律系统:如家庭法、契约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这类法律所规定的关系与大家前述的法律关系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表现出一种积极有哪些用途,表现出基本从劳动分工产生来的协作。[3]“契约事实上是协作的最高法律体现。”[2]涂尔干之所以觉得契约类法律体现的是积极团结,指合同是合同相对人主动达成的,与其利益息息有关,契约程度越高,社会凝聚力越强。也就是说,团结动力源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物的团结就没这个动力。涂尔干在法律和社会团结中,区别物的团结与人团结有重大意义,整个法学传统,对于法律中物与人这两大元素,考虑物较多,考虑人较少,涂尔干看到了二者有什么区别,可惜没展开。
涂尔干对我们的理论总结非常简洁:“规范大概是如此产生的:劳动分工越进步,规范就会变得越多――假如没规范,有机团结就是不可能的,或不健全的。”[2]涂尔干不自觉地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分析了社会分工、法律、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虽然他没明确法律的社会团结功能之类的命题,但确实革新了法学功能,对当今中国法学振聋发聩。